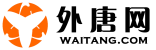俄罗斯陕西村百年历史文化纪实的相关介绍
19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陕、甘、宁地区曾发生持续十多年的回民起义,起义失败后,数千名起义军民拉家带口,一路翻山越岭,到中亚逃生,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栖息在楚河岸边时,当地的沙俄官吏便将这些来自天山东部的中国移民称作“东干人”。此后,这批陕西回族移民就与华夏大地彻底丧失了联系,成了一个栖息中亚的新民族。
一个多世纪以来,东干人一直在只有自己人居住的村庄里生活,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目前,东干人主要居住在伊塞克湖和楚河之滨,此外,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这两座中亚大都市里也有东干人聚居区。东干人在19世纪80年代约有1.5万人,目前大约有12万人。
称政府机关为“衙门”,叫媳妇为“婆姨”
东干人至今还在讲一个世纪前的陕甘地区回族方言。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政府官员称为“大人”,称店铺老板是“掌柜的”,“写家”则是指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诗人。对东干人而言,飞机仍旧是“风船”,嫁妆只能叫“陪房”。他们的汉语知识仍旧停顿在晚清年代,而他们对现代汉语几乎一无所知。东干朋友告诉笔者,东干语中的“老话”都是陕西方言,而像“芭蕾舞”、“导弹”一类的“新话”则多从俄语中转借。一般来说,除东干语外,东干族男女老少都会讲俄语。东干人也有自己的文字———用俄语字母把清代的陕西方言串联成拼音文字。回想当年,笔者还曾与埃利克一起为东干人的报纸翻译过中国民间故事———笔者将汉语原作口译成俄文,埃利克再把俄文译成东干文。据说,东干人的这种书面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得不能再好的时期,由苏联的语言学家创立的。仔细想想,这竟可以算是将汉字拼音化的一次尝试。东干人的姓名也可谓“中俄合璧”。他们都有自己的俄文名字,比如马三旗村合作社主席老吴的全名叫吴·依斯哈尔·尤素波维奇,但在东干村内,人们还保持着100多年前的习惯,称他“老吴”。
虽然当年沙俄当局给了东干人新的民族称号,希望让他们脱胎换骨,然而,东干人却有自己的文化选择。他们不仅固守自己的口头语言,而且还全力保留痛别故土时的生活习俗。正是有了他们灵魂中对传统文明不可遏制的依恋,今天踏上中亚大地的国人才会惊奇地发现,在东干人居住的楚河谷地,竟然保存着几座晚清韵味十足的“陕西村”。
走进东干人的民家小院,感觉就像到了陕西农村,那粮仓、水井、房檐上的一串串老玉米,都透着华夏文明古老的灵气。待客用的正房垒着一张大炕,热炕头的一边是装着全家细软的炕琴,正中则摆放着油渍斑驳的炕桌。盘腿坐在炕桌旁,吃上一碗男主人的“婆姨”精心拉出的面条,再伸长筷子,尝尝各种咸菜和炒菜的味道,人在国外的感觉就不知躲到了哪里。
埃利克生在比什凯克附近的“米粮川”,听村名就知道那也是一个东干村。他在莫斯科拿了语言学博士学位,成了“京城”里的“写家”,但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仍在米粮川以种菜为生。他说,东干农民家家有“拉达”汽车,户户有粮食垛。对农民来说,这日子就算不错。
埃利克曾给笔者看过他与“婆姨”的新婚照。埃利克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整个一个旧中国的乡绅。新媳妇浓妆艳抹,面若桃花,脚穿绣花鞋,头顶红花高髻,身着绣满龙凤图案的红色裙衫,极尽艳丽花哨。
据说,东干人极为看重婚礼,婚礼场面很讲排场。虽说年轻人有权自由恋爱,但婚姻大事最终要由父母一棰定音。按传统,东干人一般情况下不允许与外族通婚,新人在婚后多半要与长辈共同生活。高宅大院儿,四世同堂,多子多孙,天伦之乐。东干人说,这就是他们憧憬的幸福生活。
东干人没有更多奢求,他们认真做事,老实做人,心静如水
楚河岸边的“马三旗”和“新渠”是东干人居住的两个大村庄。村民吃苦耐劳、辛勤劳作的场面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东干人精于耕种,多以种菜为生。中亚地区蔬菜价格奇贵,东干村与比什凯克、阿拉木图这些大城市又相距不远,这样一来,种植蔬菜让东干人每年都可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与左邻右舍那些突厥族人的村庄相比,东干人的日子过得算是殷实富足。笔者的一位哈萨克朋友说,东干人的富裕日子源于他们吃苦耐劳的天性。对我们来说,东干人的钱财连同他们忙碌的身影就像是一幅漂亮的风景画,你只能欣赏,却不会对画上的景色心生嫉妒,因为你知道,苦尽甜来的感觉并非人人都能享用。
半个月前,笔者再次走访马三旗。刚把车停在村“衙门”前,就看到了去年盛夏请笔者在村东头瓜地里吃西瓜的石老头。老石并不老,也就接近50岁,风吹雨淋,面相老点而已。老石说,“衙门”就别进了,那里边没人,到家里坐坐。老石家的土坯火炕热得烫手,笔者只好侧身坐在炕沿上。老石的儿媳妇在院子里不停地忙碌,不时弄出金属器皿碰撞的声响。老石说,冬季活儿少,可也闲不着,种棚菜的,修渠的,做小买卖的,进城打工的,干啥的都有。突然大黄狗一阵乱叫,老石的孙子放学回来了。小孙子的俄语说得非常流利,能给老石当“先生”。按老石的说法,东干人当然要会说东干话,可不会说俄语却无法与外村人交流;至于学习现代汉语,那是“进大学堂,做大学问”,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就这样与老石闲聊,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里外都是东干人的故事。同中亚其他各民族一样,东干人经历了苏联时代社会生活的沉闷和平稳,也体验到苏联消亡后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和机遇。在苏联解体10年后的今天,独联体各国的老百姓开始念叨苏联那会儿的种种好处:当年整个社会的色调虽说没有现在艳丽,但大家至少都拥有平稳舒适、远近无忧的日子。东干人也对逝去的岁月依依不舍吗?老石说,苏联时期东干人就种菜,现在还是种菜,日子没啥两样;东干族的人口数量太少了,少到不可能与左邻右舍争斤论两,同时也没人有意找你麻烦,过去如此,现在还是这样。老石的看法又让笔者想起了埃利克有关这个问题的议论。埃利克说,东干人并没有被苏联时期的“大锅饭”惯坏,很快就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进入了自己的角色。中亚各国独立后,东干人踏上了名正言顺的发家致富之路,“我们不求大富大贵的奢华,只图不愁吃喝的安稳”。
站在马三旗村头的一口枯井旁,透过茂密的白杨林,笔者注视着村里一家一户的农家小院。那静静飘逸的炊烟似乎正把笔者内心一种难以言表的思绪驱散。东干人失去了很多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也没有更多斑斓灿烂的奢求,但他们仍旧认真做事,老实做人,热爱生活,心静如水,在新的土壤里迅速扎根、开花、结实。